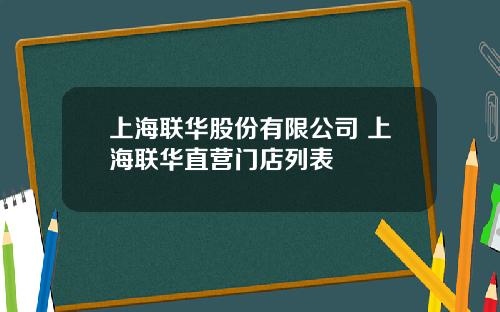近日,由归元玄奘文化促进会、中国玄奘研究中心、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佛学论坛共同主办,主题为“传承玄奘精神,弘扬丝路文化”的首届玄奘与丝路文化国际研讨会及高峰论坛在西安、商洛举行。研讨会囊括现今玄奘与丝路研究领域的主流学术和文化专家,集结出版了《首届玄奘与丝路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澎湃新闻·古代艺术”经授权刊发由贵州省博物馆助理馆员袁炜撰写的《<大唐西域记>所见西域钱币考》。作者通过考古资料、传世文献、出土文书和钱币学来考证《大唐西域记》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所见西域钱币。他认为,玄奘将其所见的西域138国流通货币分为四个部分,这些货币与当前出土中亚、印度、伊朗等区域钱币学研究相符,由此说明了《大唐西域记》对西域钱币的描述基本可靠。
《大唐西域记》是玄奘在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向唐太宗李世民上进的一部西域史地专著,玄奘将其在西域所见所闻的138个国家如实的撰写成《大唐西域记》。在《大唐西域记》中,有不少对当时西域各国流通货币的描述,通过这些描述,我们可以一窥唐朝初年中亚、印度等地各国货币流通情况。
因为在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王朝灭高昌国并以其地设西州,故玄奘以离高昌最近的西域国家焉耆为《大唐西域记》所述的第一个西域国家。但其实在玄奘途径焉耆前,他已经多次接触过西域货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言,玄奘在凉州举办法会,“散会之日,珍施丰厚,金钱、银钱、口马无数,法师受一半燃灯,余外并施诸寺。”
在两汉之时,河西地区通行五铢钱,到南北朝时期,随着丝绸之路贸易的繁盛,凉州成为西域商人汇聚的大都市。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的一个长城烽燧遗址处发现了8件粟特文信件,其中的五号信札是由居住在姑臧(今武威)的发黎呼到写给可能居住在于阗的商队首领萨般达的信件。有学者认为这封信札的年代在公元313~314年。在信件中,多次提到了一种以“斯塔特”为货币单位的银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其中还有“二分之一斯塔特银币”这样的描述。
由此看见,自4世纪初叶起,随着粟特商人对丝绸之路商业的经营,他们在如武威这样的商业城市设立商站,白银逐渐成为了丝绸之路上的流通货币。到了北周、隋唐之时,正如《隋书•食货志》言,“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 玄奘在河西凉州举办法会,西域胡商捐献西域金钱、银钱可谓是这一历史情况的真实写照。
未能释读君主姓名的中亚铜币(公元6-7世纪)
在高昌国时,高昌国国王麹文泰给玄奘,“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疋,充法师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有学者以此认为,唐初的高昌国以称量黄金、银币、“绫”及“绢”共同做为货币,而没有铜钱的流通。首先需要指出的是,“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疋”是麹文泰在玄奘离开高昌时赠送给玄奘以充当其西行求法的开支,即“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疋”是玄奘即将去的西突厥、印度各国所流通的货币,并非简单的视作高昌国以以称量黄金、银币、“绫”及“绢”共同作为货币,而没有铜钱的流通。其中,还没有铸币传统的西突厥使用绫、绢作为实物货币,中亚、印度等地使用黄金、银币作为货币。
至于当时高昌国的流通货币,则可以通过出土文献和钱币实物得到解答,有学者通过对吐鲁番经济文书的研究,指出自公元561年至680年,即麹氏高昌中后期到唐朝初年的120年间,这一阶段吐鲁番以银钱为流通货币,在唐朝灭麹氏高昌设立西州后,中原的绢帛在西州也逐渐开始承担货币职能。由此可见,在玄奘到达高昌国的时期,银币是高昌国流行的货币。再根据当今吐鲁番考古发现,可见这一时期吐鲁番墓葬中陪葬的钱币主要是萨珊波斯银币和仿制的拜占庭金币,这些仿制金币几乎都有穿孔,故其绝非作为流通货币使用,而应当是装饰品。由此可见,在玄奘到达高昌国时,高昌国使用的货币是萨珊波斯银币,而并没有称量黄金、“绫”及“绢”等货币。
萨珊波斯喀瓦德银币(488-531年)
《大唐西域记》言阿耆尼国“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阿耆尼即焉耆,焉耆国国都和其后的焉耆都督府治都位于博格达沁古城,据考古调查,在博格达沁古城采集有东汉五铢、萨珊波斯银币等钱币。这枚萨珊波斯银币是卑路斯一世时期(公元459至484年)所铸行的。在四十里城市旧城采集有金子、五铢钱。由此可见,唐初焉耆流行的“银钱、小铜钱”所对应的萨珊波斯银币和东汉五铢都已发现,但至今为止还未发现有“金币”,曾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西域各国流行的金币应当是拜占庭金币,但后又否定了自己的说法。
龟兹五铢正面
龟兹五铢背面
《大唐西域记》对龟兹国货币的描述同样是“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但需要指出的是,与焉耆铜钱流行的是东汉五铢钱不同,这一时期龟兹国所流行的“小铜钱”是一种一面有汉文“五铢”字样,一面有两个还未能释读的婆罗米文龟兹语字母的方孔圆钱。这种铜钱被当代学者称之为龟兹五铢。据考古发现,自1928年以来库车已经发现了上万枚龟兹五铢钱。由此说明了龟兹与焉耆流行的“小铜钱”并不相同。在银币方面,《周书》言,龟兹国“准地征租,无田者则税银钱”。且考古也在库车发现了这一时期的萨珊波斯银币,故玄奘所言龟兹流行的银币即萨珊波斯银币。至于金币,与焉耆国条目相同,迄今为止还未在文献和出土发现中找到这一时期龟兹国流行金币的证据。
Chaganian仿萨珊波斯库斯老一世银币(公元6世纪)
仿萨珊波斯库斯老一世银币1(公元6世纪)
仿萨珊波斯库斯老一世银币2(公元6世纪)
《大唐西域记》载覩货逻国故地“货用金银等钱,模样异于诸国。”据玄奘介绍,吐火罗故地的地理范围东起葱岭、西至波斯,南抵兴都库什山,北达铁门关。对于吐火罗钱币,苏俄学者作了不少研究。研究指出,当时吐火罗地区流行的钱币主要是模仿萨珊波斯银币铸行的银币,其上有巴克特里亚文、粟特文或装饰性纹样的戳记。但在细节上,这些模仿萨珊波斯银币铸行的银币其钱币铭文语言,君主肖像风格等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故玄奘言吐火罗钱币“模样异于诸国”。
《大唐西域记》言梵衍那国“货币之用,同覩货逻国”。梵衍那国都城即今阿富汗巴米安。在北魏时期,嚈哒盛兴,吐火罗国和梵衍那国同被嚈哒控制,通行嚈哒仿萨珊波斯样式银币,所以在嚈哒灭亡后,吐火罗国和梵衍那国依然使用嚈哒仿萨珊波斯样式银币,故其货币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在今阿富汗巴米安附近的Samingan地区发现有一大批巴克特里亚语文书,其中很多是有明确纪年的经济文书,在这些有明确纪年的经济文书中,有一些与玄奘西行的时代非常接近。在这些文书中,多次提到以“第纳尔”为货币单位的铸制金币。故在玄奘西行的年代,位于阿富汗巴米安的梵衍那国打制行用有金币,同理可推证货币与梵衍那国相同的覩货逻国故地也打制行用有金币。为何当今这些地方发现的这一时期的钱币主要是银币和铜币,金币极为罕见,笔者认为这与金币价值高,在后世很容易被销熔有关。是故玄奘描述覩货逻国故地和梵衍那国“货用金银等钱”是正确无误的,由此也可推论玄奘言焉耆、龟兹等国“货用金钱”必定是有所具指,只是这些“金币”我们现在还未发现。
《大唐西域记》载迦毕试国“货用金钱、银钱及小铜钱,规矩模样,异于诸国。”在嚈哒解体后,迦毕试成为独立的国家。其货币继续沿用吐火罗地区嚈哒样式铸造钱币,所有钱币铭文都采用婆罗米文,钱币上绝大部分的国王采用印度名称,由此可见迦毕试国的统治者已经印度化。
《大唐西域记》言印度“然其货币,交迁有无,金钱、银钱、贝珠、小珠。”值得注意的是,在玄奘自印度东归时,戒日王付乌地王“金钱三千、银钱一万,供法师行费。”将戒日王给玄奘东归的赞助与高昌国麹文泰给玄奘西行的赞助(虽说麹文泰给玄奘的经费是供玄奘往来印度二十年的费用,但印尼玄奘对沿途寺庙布施过多,在到达印度时就以用尽)相比较来看,在银币方面两者都是一万枚银币,但在黄金货币方面,麹文泰给玄奘的是“黄金一百两”,而戒日王给玄奘的则是“金钱三千”,由此可见与只通行银币的高昌不同,当时的印度金、银币同时通用。印度戒日王钱币现发现数量极少,1904年,印度北方邦发扎德巴县出土了一批钱币,包含1枚金币,522枚银币和8枚铜币,其中就有一些属于戒日王发行的钱币,由此从出土钱币上证明了在戒日王统治时期印度流行金、银币。
西北印度仿萨珊波斯银币(公元8世纪)
在使用天海海贝等作为货币方面。《通典》言印度“以齿贝为货”;《旧唐书》言中天竺国“以齿贝为货”;《新唐书》言中天竺国“以贝齿为货”;《册府元龟》言中天竺国“以龟贝为货”。据历史文献学研究,《通典》、《旧唐书》、《新唐书》和《册府元龟》对中天竺国风俗的描述基本相同,且不见于唐前诸西域传中,所据内容可能出自已经亡佚的王玄策著《中天竺国行记》。王玄策曾多次出使印度,《中天竺国行记》正是其在第三次出使印度归国后撰写的,其时间距玄奘游历印度之时不过二十年,其对中天竺国货币的记载可与《大唐西域记》对印度货币的记载互为雠校,可证戒日王统治下的中天竺国的确以海贝为货币。
《大唐西域记》言在那揭罗曷国醯罗城“诸欲见如来顶骨者,税一金钱。若取印者,税五金钱。”,玄奘在此“施金钱五十,银钱一千”。再加上后文言玄奘在犍陀罗布色羯逻伐底城时,“自高昌王所施金、银、绫、绢、衣服等,所至大塔、大伽蓝处,皆分留供养,申诚而去。”由此可见,高昌国所行用的萨珊波斯银币自高昌起,经塔里木盆地,吐火罗故地至西北印度都是可以行用的。
《大唐西域记》言羯若鞠阇国曲女城西北窣堵波的精舍中藏有佛牙,佛教信徒“欲见佛牙,轮大金钱。”《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言戒日王在举行曲女城大会前,施佛“金钱三千”,在无遮大会结束时,欲赠玄奘“金钱一万,银钱三万”。在举行无遮大会时,“人施金钱百”,《大唐西域记》载恭御陀国“国临海滨,多有奇宝,螺贝珠璣,斯为货用。”据考证,恭御陀国位于今印度奥里萨邦甘贾姆县北部,面临孟加拉湾。
由以上玄奘、王玄策对印度各地货币的记载来看,可以看到位于印度西部的那揭罗曷国主要流行金币等金属铸币,位于印度中部的中天竺同时流行金银铸币和天然贝币,而位于印度东部的恭御陀国则以螺贝珠璣为主要通货。故玄奘总称印度“然其货币,交迁有无,金钱、银钱、贝珠、小珠。”
中亚Ramik银币(公元6世纪)
中亚Bravik铜币(公元7世纪)
《大唐西域记》言波斯国“货用大银钱……户课赋税,人四银钱。”对于玄奘为何将使用波斯萨珊银币的焉耆、龟兹钱币称为“银钱”,而波斯本国使用的萨珊银币称为“大银钱”,其主要原因是,萨珊波斯银币在库思老二世时(公元591年至公元628年),做了比较明显的改动。一是在币重不变的情况下,币面直径扩大,币身变薄;二是正面用围绕君主肖像周围的连珠纹改为两圈,背面连珠纹改为三圈;三是其中后期铸币,肖像由半浮雕改为平雕;四是币的正、反两面均铸造有上下左右四组新月抱星图案。故玄奘将流行于中原、西域铸造较早的萨珊波斯银币与萨珊本土流行的新铸造的库思老二世银币视为两种不同的钱币,并认为萨珊流行“大银钱”,新疆地区流行“银钱”。就中原、新疆出土的萨珊波斯银币而言,也同样支持这一说法,如作为早期尺寸较小形的卑路斯一世银币,其在萨珊波斯的铸造时间是在公元459年至484年,在中原和新疆的埋藏时间则自公元481年至唐初;开始变薄变大的库思老一世银币,铸造时间在公元531年至579年,在中原和新疆的埋藏时间则自公元584年至7世纪后半叶;库思老二世银币铸造时间在公元591年至628年,在中原和新疆的埋藏时间则自公元626年至8世纪中叶。可见,新疆地区流行的萨珊波斯银币要比萨珊本土流行的萨珊银币迟一段时间,而这延迟则造成了玄奘认为焉耆、龟兹流行“银币”而萨珊波斯流行“大银币”。
萨珊波斯库斯老一世银币(531-579年)
此外,有关波斯国以银钱赋税的资料,可与《隋书•西域传》言波斯国“人年三岁已上,出口钱四文”相印证。这种以银钱来缴纳人头税的税收制度,其实就是萨珊波斯库思老一世(531—579)进行税制改革的成果。在此之前,萨珊向农民征税主要以实物形式征收。库思老一世为了进行税制改革,首先下令丈量土地。其次,他根据农田栽种的作物种类确定每一加里布土地征收的税额,如一加里布的小麦或大麦田征收一德拉克马赋税,一加里布的葡萄园征收八德拉克马赋税。在这种新规定下,除了贵族、战士和祭祀,所有年龄在20到50岁的人都要付人头税,税额依富裕程度而定。从4德拉克马到12德拉克马不等。可见,《大唐西域记》和《隋书》中记载的波斯国每人每年四德拉克马银币的人头税是其中税率最低的一等。
由以上可知,玄奘将其所闻所见138国流通货币分为了四个部分,一是焉耆、龟兹等塔里木盆地诸国,玄奘言其流行金币、银币和小铜钱,这里的银币是发行时间较早的萨珊币原型银币;二是位于中亚和西北印度等原嚈哒领土,玄奘言其流行金、银币,且形制不同于其它地区流行的钱币,这里的银币是嚈哒仿萨珊币型银币;三是印度诸国,玄奘言其流行金、银币以及贝币等,此处的银币是印度型银币;四是萨珊波斯国,玄奘言其流行大银币,即厚度较薄,尺寸较大的萨珊王朝晚期宽缘币型银币。这也与当前出土中亚、印度、伊朗等区域钱币学研究相符,由此说明了《大唐西域记》对西域钱币的描述基本可靠。
注:
龟兹五铢钱图片版权归甘肃钱币博物馆,其余钱币图片全部采自(乌兹别克斯坦)E.Rtveladze, Catalogue of Antique and Medieval Coins of Central Asia Ⅱ&Ⅲ, the National Bank for Foreign Economic Activity of the Republic of Uzbekistan, 2000.